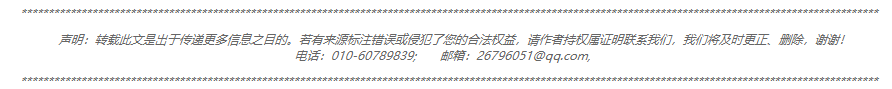古人“空桑偶得”自然发酵的酒,距今已有7000年。然而,直到明代华亭柘林人何良俊(今上海奉贤柘林镇人),在《四友斋丛说·杂记》中用了“黄酒”一词,或许命名才算乾坤已定。
笔记体的《四友斋丛说》初刻于隆庆三年(1569年),其“杂记”部分有这样的记载:“即同至酒店中唤酒保取酒。酒保持黄酒一大角,下生葱蒜两盘,即团坐而饮。”寥寥数语,内容却十分丰富,它被《辞源》“黄酒”一词释为首例,可见其权威性。
“黄酒”之名虽然迟到,文字记载的酒:“臣请荐脯,行酒二觞”出现在《吴越·春秋》中,至今却已有2500年。那时的酒或许是“浊酒聊可恃”“三杯两盏淡酒”“一杯薄酒休辞醉”……这些“会须一饮三百杯”的酒,虽是诗人的夸张,倒也说出了酒之初是浊酒、淡酒、薄酒,是“醪醴之味”,与甜浊的家酿米酒相似,而与如今“酸甜苦辣咸鲜”六味齐全的黄酒,则相去甚远。
由此要问:从米酒到黄酒的蜕变究竟在何时?遍翻涉及酿酒的著述,从我国现存最早的农学著作、北魏的《齐民要术》,到北宋的《北山酒经》;从明代的《本草纲目》《天工开物》,到养生专著《遵生八笺》等等,面对卷帙繁复的古代酿造技术,有专家说,作为一种猜测,类似绍兴黄酒的工艺,很可能在南宋时就已基本成型。这一模糊说法,令人难以释然。同时,承载着诗人和文武之道的酒,随着世事巨变,其作用是否也有各种变化?疑问种种,或许我们能借诗人的作品窥其一角,截获这些演变的若干端倪。
诗酒相亲,“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自始至终都和酒文化勾连在一起”,它是中国文学最具浪漫色彩的部分。酒之初,以祭祀起,然而在最早的文学作品《诗经》中,酒字出现了63次,尤其是《小雅·宾之初筵》,全诗五章,描述了上层贵族饮酒、醉酒的完整场面,第三章写了未醉到醉的过程,节奏滞缓,这一“侧面”,或许与酒之淡薄有一定关系。酒与诗的关联发端于《诗经》,到了曹操的《对酒》《短歌行》等,有了“慨当以慷”以解“天下归心”之忧的意思,自此,酒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“玉浆”。当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嵇康、刘伶等饮酒之诗和《酒德颂》的出现,“衔杯漱醪”,唯酒是务,借酒浇愁,酒也成为避祸之“利器”。与他们不同的是,晋末大诗人陶渊明的《饮酒诗二十首》,他归隐田园,虽“偶有名酒,无夕不饮”,诗中表达的意思却是高洁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,或许这也是他所说的五味杂陈的“酒中有深味”。
唐朝诗人的饮酒诗浩如烟海,名篇迭出,令人目不暇接,而诗仙李白的《将进酒》是其中的最高峰,把“人生得意须尽欢”和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组合在一起,一举将酒的品质和喝酒时的状态,黄河之水般倾泻而出,磅礴之势,无人能出其右。而李白在《客中行》中一句“玉碗盛来琥珀光”,则描述了使人艳羡的美酒之色,它如此接近黄酒的“标准色”,或许也为之后的黄酒,奠定了酝酿方向。与唐诗一样,宋词也是无酒不欢,辛弃疾的“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”;柳永的“今宵酒醒何处?杨柳岸晓风残月”;苏轼的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”等等,都是名句名联。更有陆游《钗头凤》里的“红酥手,黄縢酒。满城春色宫墙柳”,描述了自己与原配唐氏被迫分开后的相思之情,此曲催人泪下,也标配了酒在爱情诗上的独特作用。
诗与黄酒几乎相当于“同胞手足”,而黄酒,如同诗歌的多样化,并非只有琥珀色、淡黄色,它还有褐色、黑色、红色、棕色等。笔者近年曾专程去温州泰顺,觅得当地原住民自酿的红色黄酒,它的酿制过程与其他黄酒基本一致,只是酒曲用了当地传统的红曲。而来自山东即墨的黄酒则呈黑红色。这些似乎印证了黄酒界一位前辈的说法,黄酒之黄,并非只指酒的色泽,还包含有炎黄子孙的“黄”、黄色人种的“黄”、祖先发源于黄河流域的“黄”。黄酒是炎黄子孙的酒、中华民族的酒。
正值新年,把酒言情之际,也需要知道,这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有力象征啊。(完)